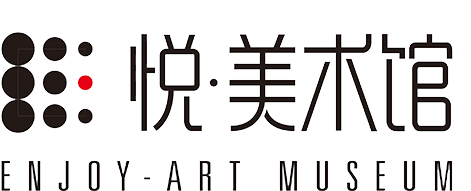访谈|刘㔻+成蹊+冉修

海报设计:聂峻
成蹊:本次展览题目来自刘㔻在角落中拍的一张照片,上面写了这几个字“小刘工作干不好”,当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想到的是一个人凝固的瞬间。刘㔻这次个展其中一个版块的题目叫“认领”,他认领了生活中一个瞬间的场景作为题目,其实他认领的不仅是一件作品,同时也认领了一段人生的存在。如此偶然的相遇,这与刘㔻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如果把这句话分开来看“小刘、工作、干不好”,这三个词正好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
(一)“小刘”是关于身份问题
成蹊:小刘可能是艺术家,也可能是快递小哥、医生、教师、音乐人、程序员,小刘可能是儿子,也可能是父亲、母亲、老板、下属、恋人、仇人等等。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小刘”,一百个“小刘”也就有一百个人生。
1,因此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你跟“小刘”的关系,偶然的相遇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规律?
刘㔻:那天我开车无目的转悠,在城中村里一条颠簸的脏路那儿靠边停了。周围挺多运渣土的卡车来来往往,一个废弃的幼儿园铁门被锁了,然后旁边一个特小的小区孤零零的在路一侧……里面只有一栋三层的居民楼。我步行走到最尽头想着能不能绕到楼的后面看一下,结果通道被一些垃圾还有废弃的建筑材料给封堵住了。当转身准备折返时,看见最靠内侧的一个单元口内赫然写着这八个字:“小刘工作干不好”,其实那一瞬感觉挺逗的,感觉像某个领导、上级或老师的腔调。而且觉得好像还有下文没说呢……就是一个气口在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情景表情凝固住的那种。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毕竟感觉也像是对我说的……
其实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与各类人经常打交道,难免会碰到同姓的。或对方称呼我“小刘”,或我称对方“小刘”。“小刘”只是一个代号,我个人跟小刘的关系表面上来看更多是年龄层面的。现在叫我“老刘”的逐渐多了起来,当然也有人爱叫“刘总”、“刘老板”或“刘老师”的。
你说的没错,往深去看“小刘”确实是指向了一个身份问题,而如何看待这个身份称谓某种程度上又极大的取决于我们的身份视角。 偶然的相遇背后当然存在着必然性。过去,我与我自己以及其他很多个活生生不同背景的“小刘”相遇过,未来我依然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小刘”,他们都在不远处等着我……
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作品名:腿间耳 材料:逐帧动画 尺寸可变
2,艺术的问题是不是首先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刘㔻: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并不明确这是不是必须只能由艺术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大部分出色的艺术作品都是很好的拷问了“我与当下环境”和“我与人群”这两个问题。在这样的范畴内提出质疑、拓展认知以及丰富角度。至于“我与自己”的问题,除非希望让其可被识别,否则……是不是艺术的作为已不太重要,或者说这个问题已无需依附于艺术来探讨。通常情况下,能够真正长久深入自身的人是并不会有特别强的表达意愿的,更谈不上使用某种媒介手段去呈现什么作品来进行展示,这里所说的是“真正的”。但认识洞察自身、观照内心,是做艺术必备的先决条件。
3,你跨界身份是如何形成的,是你主动选择还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刘㔻:绘画,这是我从小就痴迷热爱的事情,意义不明。画家,是我之后受训的绘画专业初始身份。因视觉领域的相关性而牵扯出了其他更具商业变现能力的新身份:美术指导、CG主美、原画师、动画导演、设计师、视觉总监等。这些相关身份与画家的角色有很大不同。画家是非常个人化私密化的且并不解决社会有效问题的。而这些新身份之所以有很强的商业变现能力,都是因其能够解决具体问题为前提的,都是具备“服务意义”的。也是因为这一点而更加容易与其他领域相接壤也促使我逐渐衍伸出新领域的其他新身份:投资人、公司股东、部门经理、战略师、投机者等等…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从事乐器演奏是有内心意愿驱动的,是意义不明的。出于对四肢协调性的迷恋使我在音乐领域的初始身份是鼓演奏。而如果将这一身份嵌入“服务意义”则是鼓手。鼓手具体的解决音乐中尤其是歌曲中的节奏部分,是解决有效问题的。但,鼓本身的语言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存立的。也正因这个视角,渐渐让我觉得鼓的更大能量并不局限于歌曲这一单独语言内,于是触手也就伸展到两大非歌曲领域中…爵士器乐与实验器乐。在非歌曲领域,鼓演奏则很少解决有效问题且不再停留于“服务意义”中。以上这些除了初始身份有些意义不明之外,其他的是我主动选择而导致的结果。我更愿承认是我将自身相嵌进具体的“服务意义”中顺其自然而得来。就像这些也会顺其自然得来“艺术家”这个身份一样。
我在2015年与2020年先后组建两支组合:
实验器乐组合:发梦茱莉,
爵士器乐组合:朝西门顺。
组合名:发梦茱莉 视频场地:今日美术馆
组合名:朝西门顺 视频场地:OMNI SPACE
4,你如何看待你的多重身份,最喜欢哪个身份?你是享受其中还是经常迷失找不到自己?
刘㔻:我对我的身份总体做了两大类划分,即具备现实意义的与不具备现实意义的。前者有具体的利润生产方式,沉浸于现实社会解决具体问题获得具体物质回报。后者彻底背道而驰,随时从现实社会抽身并顽固的只考虑精神表达与体现。也就是社会化的与反社会的两种存在。迷失没有,但也不能说是享受……我只是觉得可惜了一些损失掉的时间以及对自身的消耗,而那些消耗是不可逆的。
5,从你的多年的跨界艺术实践经验来看,艺术有边界吗,边界在哪?
刘㔻:艺术没有边界,所谓的边界只是当下人们对于艺术的定义以及所看待的眼光。
正是那些范式或为了打破范式的范式造就了边界。
DRUM SOLO 视频场地:VIBEZ STUDIO
(二)“工作”是关于认知的问题
1,艺术是工作吗?
刘㔻:艺术是工作。
虽然并不解决具体问题,也没有具体目标,更没有实质的具体答案。完全意义不明,但依然是工作,只是不太像通常定义下的“工作”。
2,你如何认定你的工作是艺术行为?
刘㔻:在我不以服务的意识与物质的交换作为量化标准的情况下,只顽固遵从内心意愿去做的工作行为。
(三)“干不好”是关于方法的问题
成蹊:艺术上的如:观念、语言、技术、媒介、表达等问题,生活也同样存在观念和技术的问题,你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刘:生活是一盘棋,宏观看待而微观的去体验。我在生活中的观念更多时候是倾向于跨越时间的,技术服从于这个观念。具体说就是,动态的利用我这个工具去完成我的背后力图完成的事项,当下只是渡过。

作品名:Flesh can’t fly 材料:布面油画
尺寸:94cmX70cm

作品名:happy PIG year 材料:布面油画
尺寸:135cmX135cm
策展人 冉修 提问:
冉修:1,这次个展可以看做是对你近年艺术工作的一个回顾和总结,个展题目“小刘工作干不好”除了表面的自嘲之外,更有一种自省意味,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次展览或者说这些年的创作?
刘㔻:近年的创作基本都在围绕着如何能够整合使用我的能力,在来来去去的推敲实践中会意识到我这个个体在中间掺杂了多少因素。于是渐渐的开始落实从自身的处境与体验中出发,去体会个体的感受而不太关注那些宏大的、集体的或新奇的事物。我是一个比较讲究手感的人,相较新媒介而言很多旧材料我反倒更热衷。无论是绘画、逐帧还是乐器等等……
那些单纯的大词离我越来越远,而大词下的技术离我越来越近。我不会抗拒,会选择顺应这些技术并试图利用好它们给我带来的自身更新。这次个展确实是一个阶段性总结,之后路还很长,继续前行就是了。
作品名:驾崩的蝇 材料:纸本钢笔
2.除了艺术工作之外,你在不同的领域还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它们使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艺术,这一点在作品中体现的比较明显了。在我看来或许是因为你的美术指导身份使你对日常生活场景据有超常的敏感性,因此才有了认领系列作品;打鼓的行为作品显然是你作为鼓手身份对艺术的介入……
但是我的问题是,既然你有这么多工作,为什么还非要做这个艺术工作?换句话说,你做艺术的冲动力来自于哪?或者再问的直接一点,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当代艺术家了,为什么还缺你一个?在我看来认清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刘㔻:我对艺术的冲动力首先来自于热爱,而我也从未觉得这份“热爱”廉价,在我看来这份热爱犹为重要。再者,我也不愿以浑浑噩噩的过活为目的,因为有太多可以“过活”的方式了,但并不能支持我前行。至于艺术家这一冠名并不重要,因为艺术并不能被艺术家这一称谓或职业所代替。更多所谓的艺术家们并不是想做艺术而是想做艺术家,他们对于艺术毫无热情,也不关心艺术是什么,甚至把个人判断、喜好也放在一边,只是行业的初级生产者。所以缺不缺我这一个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作品名:腐败的鱼 材料:纸本钢笔
3. 你前面说艺术是没有边界的,那你怎么看待艺术和大众文化?你的艺术工作和其他领域之间有边界吗?
刘㔻:艺术可以囊括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无法囊括艺术。在这之间去具体消弥掉界限的人是艺术家。我的艺术工作与其他领域之间没有边界,但是反过来却有……也就是我在其他领域的工作与艺术之间有边界。
4.今年的疫情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㔻:今年的疫情影响了一些我其他的工作,倒并没有影响我做艺术的工作。除此之外,原来的出行计划,也受到了极大影响。最大的感受是人要有所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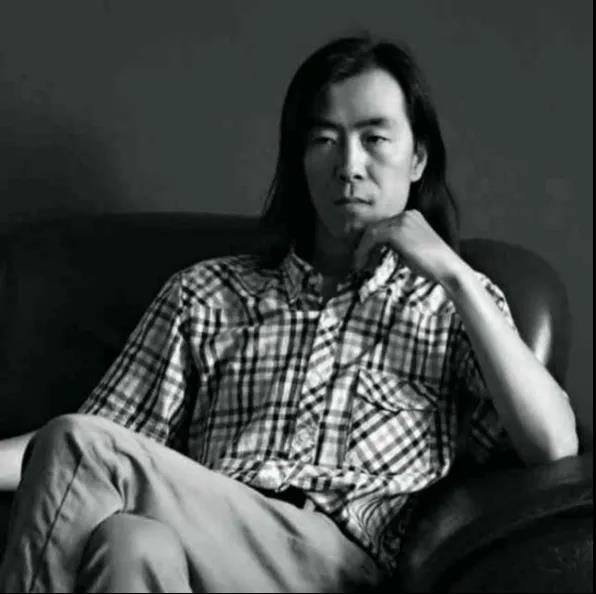
学术主持:
成蹊 1974年生于辽宁,悦·美术馆副馆长、策展人。

策展人:
冉修 1987年生于黑龙江,中央美院博士在读。

艺术家:
刘㔻 1978年生于上海,中央美院油画专业/南加大艺术学院MFA。画家、动画师、音乐人、鼓手。